Gemini_人类发展科技发展工业最终是为了什么 对话导出 (scroll)
抛出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的和“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式社会
Gemini描绘赛博朋克社会的发展逻辑
我作为人类从中寻找漏洞并进行反驳
Gemini再从我的补丁中寻找漏风点
我再去针对性的打补丁
…………
实际上就是人机辩论赛了
遗憾的是因为认知水平的不足,作为人类到最后被“击败”了,最后一张牌,劳动实现个人价值被“安慰剂劳动”驳倒,拼尽全力,无法在预设的条件下规避赛博朋克社会
迫不得已使用了最终武器——引入生产资料公有制
也就是另外开辟赛道,搬出了共产主义
严格来说属于作弊了,尽管既有的问题没有消失,不过确实从根本上破解了“高科技低生活”,消弭了赛博朋克式社会的存在基础
导出时间:20251030_204822
回合 1
用户:
>>人类发展科技发展工业最终是为了什么 人类发展科技发展工业最终是为了什么
AI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根本性的问题。从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科技和工业的最终目的,是一个从“生存”走向“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理想中的“终极目的” 和 现实中的“复杂动因”。
理想目的:满足需求的“阶梯”
如果用一个理论框架来概括这个“终极目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模型。人类发展科技,就是为了在不同层面上,更高效、更广泛地满足全人类的需求。
1. 生理需求(基础生存): 这是科技最初始的动力。
· 农业技术(如化肥、灌溉)是为了让我们不挨饿。
· 纺织工业 是为了让我们不挨冻。
· 建筑技术 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安全的居所。
· 基础医疗(如疫苗、抗生素)是为了让我们能活下去。
2. 安全需求(免于恐惧): 在生存之后,我们追求稳定和可预测性。
· 医疗科技(如现代外科手术、诊断设备)让我们免于对疾病的恐惧。
· 交通技术(如汽车、高铁)提供了高效可控的出行,(理论上)也让我们更安全。
· 信息技术(如天气预报、灾害预警系统)帮助我们规避自然风险。
3. 社交与归属需求(建立连接): 人是社会动物,科技极大地重塑了我们的连接方式。
· 通信技术(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智能手机)让我们能与远方的亲友保持联系。
· 社交媒体 满足了我们分享、被看见、寻找群体的渴望。
4. 尊重需求(获得认同): 我们追求成就感和来自他人的尊重。
· 自动化和生产力工具(如电脑、软件)使个人能完成更复杂的工作,创造更多价值,从而获得职业成就。
· 教育技术 让知识更易获取,帮助人们提升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
5. 自我实现需求(成为“我”): 这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即充分发挥个人潜能,追求创造、美和真理。
· 科学探索(如太空望远镜、粒子对撞机)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探索“我是谁,宇宙是什么”。
· 人工智能(AI) 既是效率工具,也是探索“智能”本质的哲学工具。
· 艺术与内容创作工具(如数码相机、编曲软件)让更多人有能力去创造和表达自我。
所以,从理想的角度看,科技和工业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物质极大丰富、风险极大降低、连接极其充分的世界,从而将尽可能多的人从繁重的生存劳作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
️ 现实动因:复杂的“罗生门”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复杂。在真实世界中,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还被其他强大的力量驱动,这些力量有时甚至会背离那个“终极目的”。
· 资本的逐利性: 工业和科技首先需要巨大的投入,而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增值和回报。这导致了“效率至上”,有时会牺牲工人的福祉、环境的可持续性,甚至产品的长远质量。
· 权力的博弈: 在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科技(如军事技术、航天技术、芯片技术)是竞争和博弈的核心筹码。这种竞争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迭代,但其首要目的并非“全人类的福祉”。
异化与失控(“科技反噬”):
· 工具变目的: 我们发明社交媒体是为了连接,但最终可能被“算法”和“流量”所困,反而变得更加焦虑和孤独。
· 效率的陷阱: 我们发明工具是为了节省时间,但工具的进步(如即时通讯)反而让我们陷入了“7×24小时”待命的状态,时间更不够用了。
· 精神的空虚: 就像你之前提到的,当物质需求被过度满足,而精神追求没有跟上时,人可能会陷入一种“社会自恋”,失去与自然和真实世界的连接,最终成为技术的附庸,而非主人。
总结
人类发展科技和工业的最终目的,始于对“生存”的渴望,归于对“意义”的追寻。
它是一个双重叙事:
1. 光明的叙事是: 我们在一步步“克服自然局限”,将人类从必然性(如饥饿、疾病、劳作)中解放出来,去奔向“自由王国”(从事创造、探索和思考)。
2. 警示的叙事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不要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我们必须不断反思,技术究竟是让我们变得更自由、更完整,还是让我们变得更受束缚、更空虚。
最终,科技和工业只是工具,它们能达成的“目的”,取决于使用工具的我们,选择去往何方。
你之前提到自己对“模板僵化”的担忧,这其实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相通的。你害怕的是自己变成了那个“只顾手段、忘了目的”的人。保持这种自省,本身就是对抗僵化、确保自己始终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最好方式。
你是否想进一步聊聊,在个人层面,我们该如何在这种“科技洪流”中保持清醒和方向?
回合 2
/strong>
用户:
>>未来是否存在科技极大发展,但是科技的发展并没有为普通人类的生活质量带来任何的提高,甚至在科技的加持下,虽然生产力高到不需要任何人劳动都能养活全人类,但是普通人堕落到只能维持最基本的苟活,没有任何在生存上的提升,甚至都无法保证安全,即,高科技低生活 未来是否存在科技极大发展,但是科技的发展并没有为普通人类的生活质量带来任何的提高,甚至在科技的加持下,虽然生产力高到不需要任何人劳动都能养活全人类,但是普通人堕落到只能维持最基本的苟活,没有任何在生存上的提升,甚至都无法保证安全,即,高科技低生活
AI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且令人警醒的设想。
你所描述的这个未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它已经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赛博朋克”(Cyberpunk)。
这个词的核心标语,正如你所洞察的,就是 “高科技,低生活”(High Tech, Low Life)。
你所设想的这个世界,是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严重关切的“陷阱”。它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基于当前几种趋势的逻辑推演。
为什么这样一个生产力极高、但普通人生活质量极低(甚至无法保证安全)的世界是可能的?
1. 核心问题:生产力与分配的脱钩
你设想的前提是“生产力高到不需要任何人劳动都能养活全人类”。这是一个关键点。在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能提高,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具有价值。
· 过去: 资本家(或系统)需要工人的体力、农民的耕作。为了让你更高效地劳动,系统“愿意”为你提供教育、医疗和安全(即“生活质量提升”),这是一种“投资”。
· 未来(你设想的): 当AI和自动化可以包揽一切时,绝大多数普通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可能趋近于零。
一旦一个普通人对“生产”不再必需,那么从纯粹、冷酷的经济理性出发,系统就没有动力去“投资”你的生活质量了。 你的医疗、教育、安全,都从“投资”变成了“纯粹的成本”。
2. “无用阶级”的困境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提出了一个刺耳的概念:“无用阶级”(The Useless Class)。
“苟活”的逻辑: 在你描述的未来,控制着AI和自动化生产资料的极少数精英,他们掌握了所有的产出。他们为什么还要“养活”这些对生产毫无用处的普通人?
可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残余。
可能是为了社会稳定,防止暴动。
因此,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极低水平的“全民基本收入”(UBI)或生活必需品,其标准就是你说的 “苟活”——恰好让你饿不死,但仅此而已。
3. “高科技”的应用方向:控制而非服务
在这种“高科技、低生活”的社会,科技的流向会发生分化:
服务于精英的科技: 永生技术、基因编辑、私人武装、太空旅行、奢华的“安全泡泡”(gated communities)。
服务于大众的科技:
· 不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 精英阶层没有动力去改善大众的公共住房、公共医疗或社区安全。
· 而是为了维持稳定和控制: 科技将被用于无处不在的监视系统、算法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廉价的、令人上瘾的“精神鸦片”。
4. “低生活”的具体体现:面包与马戏
这就是“低生活”和“无法保证安全”的来源:
· 精神的“苟活”: 为了让这些“无用”且“苟活”的大众保持稳定,系统会提供大量的、廉价的娱乐。这就是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Bread and Circuses)的现代版。
例如,让所有人廉价地接入一个极度发达的“元宇宙”或虚拟现实。人们在VR中可能是超级英雄或亿万富翁,但回到现实,他们依然睡在狭小、危险的“胶囊”里,靠营养膏维持生命。
· 安全的崩溃:
精英们生活在守卫森严的“绿色地带”,他们不关心“低生活区”的治安。
大众对系统而言没有价值,因此他们的安全也变得廉价。科技(如自动化警察、无人机)被用于镇压威胁系统的骚乱,而不是保护个体公民免受彼此的伤害。
结论:这不是必然,而是选择
你所担心的“高科技,低生活”的未来,是 “技术乌托邦” 走向了它的反面—— “技术反乌托邦”(Technological Dystopia)。
这说明了一个核心观点:科技只负责“提高效率”,它不负责“回答目的”。
我们上一轮讨论的“人类发展科技的最终目的”——如果那个目的是为了“自我实现”和“解放全人类”,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同步建立起社会结构、法律和伦理的“护栏”,去强制性地(例如通过税收、再分配、所有权改革等方式)让科技的红利被所有人共享。
如果我们失败了,或者我们放任不管,那么你所描述的那个“赛博朋克”式的未来,就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非常可能的结局。
你对这个“赛博朋克”的未来图景,有什么具体的部分最让你感到担忧吗?是精神的堕落,还是安全的缺失?
回合 3
用户:
>>在这种社会下,生产资料高度发达,如果只是给普通民众仅仅苟活的资源,是否会出现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无法被消费,造成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整个社会崩溃,秩序重建,重建后应该就可能避免再造一个赛博朋克社会了吧 在这种社会下,生产资料高度发达,如果只是给普通民众仅仅苟活的资源,是否会出现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无法被消费,造成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整个社会崩溃,秩序重建,重建后应该就可能避免再造一个赛博朋克社会了吧
AI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且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推演。你的直觉是敏锐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确实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然而,在“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模型中,这个经典的经济危机循环可能不会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发生,或者说,这个系统可能已经“进化”到可以规避这种特定类型的崩溃。
为什么1930年代的“大萧条”模式可能不再适用?
1. 1930年代的逻辑:大众既是工人,也是消费者
1930年代的危机,其核心是“大众”的双重角色崩溃了:
· 作为工人: 机器替代了工人,工人失业。
· 作为消费者: 失业的工人没有钱,无法购买机器生产的商品。
结果: 商品堆积如山,工厂倒闭,恶性循环。
在这个模型中,资本家需要大众来“消费”他们生产的东西,以实现利润。 亨利·福特(Henry Ford)之所以要给工人发高工资,就是为了让他们买得起自己生产的T型车。
2. 赛博朋克“新经济”的逻辑:大众不再是必需的消费者
在你所设想的“高科技、低生活”未来,这个逻辑被打破了。生产力(AI、机器人)和控制生产资料的精英阶层,可能不再需要大众扮演“消费者”的角色。
这个社会的经济可能分裂成两个几乎不相干的“闭环”:
闭环 A:精英经济(The “High Tech” Economy)
· 生产者: AI 和自动化机器人。
· 消费者: 极少数的精英阶层(可能占总人口的1%甚至更少)。
· 商品: 这才是关键。他们消费的不是“普通人生产的商品”。他们消费的是:
· 定制化奢侈品: 基因编辑、生物工程(如永生)、定制的AI伴侣。
· 服务: 由AI和机器人提供的、极其复杂和个性化的服务。
· 资源和权力: 太空领土、数据霸权、私人军队(机器人军队)。
· 体验: 真实的、凡人无法企及的体验(比如在火星上度假)。
这个“精英闭环”内部可以实现自我循环和“经济繁荣”。它生产它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自己消费掉。
闭环 B:大众经济(The “Low Life” Management)
· 生产者: 同样是AI和自动化机器人。
· 消费者: 占人口99%的普通大众。
· 商品: 这不是一个以“利润”为目标的市场。这是一个以“稳定”和“控制”为目标的管理系统。
· 大众被提供的“苟活”资源(如营养膏、廉价电力、VR接入权),其生产成本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下几乎为零。
· “生产过剩”不再是问题: 当生产成本趋近于0时,“过剩”这个概念就消失了。给10亿人提供营养膏和给1亿人提供,对AI工厂来说没有区别,只是一个参数设置。
· “消费不足”不再是威胁: 精英阶层根本不指望从大众身上“赚钱”。大众的“消费”不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而是为了消耗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防止他们惹麻烦。
结论就是: 1930年的大萧条,是“大众市场经济”的崩溃。而“高科技、低生活”的社会,可能已经抛弃了“大众市场经济”。它更像是一个“科技封建制”——精英是领主,大众是依附于领地的“农奴”。领主不需要农奴去“消费”,只需要他们活着、被控制住。
3. 那么,这个社会会崩溃吗?
它依然会。但很可能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这种经济危机,而是因为其他更根本的矛盾:
· 精英内部的斗争: 这是最有可能的。当外部(大众)的威胁消失后,精英内部会因为资源、权力和意识形态(比如“如何管理大众”)而分裂,爆发内战(高科技战争)。
· 系统的“技术性”崩溃: 比如,一个失控的AI、一场无法控制的基因瘟疫、或者极端环境的崩溃。
· 人性的反抗(黑天鹅): 尽管被“精神鸦片”麻痹,但只要有“人”存在,就总会有“觉醒者”。当这个系统出现裂痕时(比如精英内战导致控制力下降),反抗就可能发生。
4. 重建后会避免吗?
这可能是最悲观的部分。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类很难真正“吸取教训”。
假设这个赛博朋克社会真的崩溃了(比如一场核战或AI战争),幸存者们重建了社会。他们会怎么做?
· 选项A(理想主义): 他们深刻反思,认识到是“技术”和“不平等”导致了毁灭,于是建立一个更平等、更注重人文、甚至限制某些技术(比如《沙丘》里禁止“思考机器”)的新文明。
· 选项B(现实主义): 幸存下来的人,很可能是最“高科技”、最“低生活”(即最坚韧、最不择手段)的人。他们掌握着旧时代的技术知识。在重建过程中,为了“效率”和“安全”,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再次使用那些强大的技术(AI、自动化、监控)。
只要“极少数人能掌握远超多数人的力量”这个技术基础还存在,只要人性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还存在,那么重建的社会就极有可能只是在重复上一个循环,最终再次滑向赛博朋克的形态。
所以,你对“大萧条”的联想是对的,但那个“病症”可能已经被这个“新系统”用更极端的方式“治愈”了。
这是否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大众不再是“劳动力”也不再是“消费者”,那么大众存在的“价值”本身,将由谁来定义?
回合 4
用户:
>>请解释一下你提出的这个更根本的问题 请解释一下你提出的这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回答:
这是一个极度关键的问题,它触及了我们文明的根基。
我之所以提出它,是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的“价值”都是被一个外部系统(社会、经济、国家)来定义的。而这个定义几乎总是与“有用性”(Utility)挂钩。
当你从一个系统(比如“赛博朋克”社会)中抽离了普通人的“有用性”(既不能劳动,也不需消费)时,你就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哲学真空。
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分层含义:
1. 历史上的价值:人 ≠ 有用的人
在历史上,一个“人”的价值很少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它总需要被“证明”。证明的方式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
· 封建时代: 你是农民,你的价值是纳税(粮食)和服役(当兵)。
· 工业时代(资本主义): 你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作为劳动力(生产者): 你是生产线上的一个“齿轮”。你的价值体现在你的生产效率上。(Source 4.1, 4.2: 经济学讲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作为消费者: 你是市场的“需求端”。你的价值体现在你的购买力上。(Source 4.3: 市场上的供需关系是由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所驱动的。)
社会(集体)主义: 你的价值体现在你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上。(Source 5.1: 人的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社会价值是人对社会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贡献。)
你看,无论是哪种模式,你的“价值”都是由你能做什么、能贡献什么来定义的。你是一个“工具”(Instrumental Value),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国家富强、资本增值、社会进步)。
2. “高科技、低生活”的真空:价值的崩塌
现在,我们进入你所设想的“高科技、低生活”社会:
· 劳动力价值 = 0: AI和机器人比你做得更好、更便宜、更高效。
· 消费者价值 = 0: 精英经济形成了“闭环”,他们不需要你来购买产品以实现利润。
这就是那个根本性的问题:
当一个系统既不需要你的“劳动”(生产),也不需要你的“欲望”(消费)时,你在这个系统中的“价值”从定义上就消失了。
这时,“谁来定义你的价值”就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3. “价值定义权”的归属
如果这个“价值真空”出现,权力(也就是“定义权”)的归属将决定普通人的命运:
· 选项 A:“定义权”在精英手中(“高科技、低生活”的结局)
– 如果“价值定义权”仍然掌握在控制系统的少数精英手中,那么他们的定义会是纯粹的“功利主义”:
– “这些人(大众)对系统无用。”
– “无用”就等于“没有价值”。
– 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不需要投入资源去维护它的“质量”(如安全、尊严、教育),只需要保证它不“出问题”(提供“苟活”资源和“精神鸦片”)。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赛博朋克结局。大众的价值被他人(精英)定义为了“零”。
· 选项 B:“定义权”回归个体(“后工作社会”的理想)
这是另一种可能的未来,也是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正在呼吁的“后工作社会”(Post-Work Society)。(Source 2.1, 2.2)
这个模型的逻辑是:
– 切割价值与工作: 我们必须彻底打破“人的价值 = 经济效用”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陈旧等式。
– 重新定义价值: 人的价值不再由“外部系统”定义,而是回归“内部”。(Source 3.2, 3.4: 人的价值是“内在的”、“固有的”、“无条件的”,仅仅因为“你是人”而存在,这被称为“内在尊严”(Inherent Dignity)。)
– 谁来定义? 答案是你自己。
· 新的价值标准: 在这个社会里,AI和自动化负责“生产”(满足生存需求),而人类负责“存在”。你的价值体现在:
-你的创造力(从事艺术、音乐、写作)
-你的同理心(照顾他人、维系社区、建立情感连接)
-你的好奇心(探索哲学、科学、宇宙)
-你的自我实现(学习、成长、体验)
(Source 2.1, 2.2: 在一个“后工作社会”,工作不再是经济必需品,而是一种个人和创造性的选择。价值由创新、探索和创造的能力决定,而不是劳动时间。)
总结
所以,我提出的那个“更根本的问题”,其核心是:
我们是“人”(Human Beings),还是“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是有“用途”的,是服务于经济的“工具”。当“用途”消失时,“资源”就会被抛弃。
人:是有“尊严”的,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工具。(Source 1.4: 哲学家康德区分了“价格”和“尊严”。有价格的东西可以被替换,而有尊严的人,是无价的,不可替换的。)
你所设想的“高科技、低生活”的未来,就是一个系统仍然把人当作“人力资源”,但发现这种资源已经“过时”了的世界。
要避免这个未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全社会层面,把对人的定义从“人力资源”(看你能做什么)彻底转向“人”(看你是什么)——即拥有“内在价值”(Inherent Worth)的个体。
我们是否应该现在就开始讨论,当AI包揽一切“工作”后,社会应该如何重塑我们的教育、文化和经济体系,来保障这种“内在价值”?
回合 5
用户:
>>选项B中的新的价值标准中,人类的价值举例,这些项目似乎都可以被更高级的AI取代,甚至有些创造力目前的弱人工智能就已经可以做到了,如果这些价值也全部都能被ai取代,那么会不会导致选项B设想的崩溃,不可避免的滑向选项A 选项B中的新的价值标准中,人类的价值举例,这些项目似乎都可以被更高级的AI取代,甚至有些创造力目前的弱人工智能就已经可以做到了,如果这些价值也全部都能被ai取代,那么会不会导致选项B设想的崩溃,不可避免的滑向选项A
AI 回答:
你提出的这一点,是这个问题的“终极拷问”。
你完全正确。
我之前在选项B中举的例子(创造力、同理心、好奇心)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依然是基于“功能”或“产出”(output)来定义价值。你敏锐地指出了这个漏洞:如果AI在“功能”上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那么这个价值标准就会再次崩溃。
是的,如果人类的价值锚点还是“我能做什么(What I can do)”,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滑向选项A。
因为“能做什么”是一个客观的、可衡量的标准。在“产出”和“效率”这条赛道上,一个经过优化的AI(客观)最终一定会战胜一个未经优化的人类(主观)。
“大转向”:唯一的“防火墙”
要避免滑向选项A,人类文明必须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价值大转向”(The Great Redefinition)。我们必须把价值的锚点从“客观产出”转向“主观体验”。
这是唯一的“防火墙”。
让我来解释“AI”和“人”在这个新标准下的根本区别:
1. AI 是终极的“客体”(The Object)
· AI可以创作艺术、谱写音乐、模拟共情。但这一切都是“产出”,是“表演”。
· AI生成的艺术,是用来给“人”看的。
· AI模拟的共情,是用来给“人”感受的。
· 它本身不是体验者。它没有“哇,这幅画太美了”的主观感受。它没有“我很高兴能帮到你”的内在满足。它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和“镜子”。
2. 人是唯一的“主体”(The Subject)
· 在新的价值体系里,人的价值不是因为他能画出多好的画,而是因为他能“欣赏”画。
· 人的价值不是他能提供多么完美的“共情”,而是他能“感受”到爱与被爱。
用你的例子来拆解:
你担心AI会取代这些“新的价值标准”,我们来看看:
1. 关于创造力:
· 旧标准(A选项): AI画的画比我好,我(作为画家)没价值了。
· 新标准(B选项): AI能画出100万张完美的画,太好了。这并不会阻止我去涂鸦——因为我涂鸦的目的不是为了“产出”一张能卖钱的画,而是为了享受“涂鸦过程中的那份宁静和自我表达的快乐”。那个“快乐”本身,就是价值的全部。AI可以产出,但它不能“享受”。
2. 关于同理心/共情:
· 旧标准(A选项): AI治疗师比人类治疗师更懂“话术”,更高效,人类治疗师没价值了。
· 新标准(B选项): AI可以提供完美的“陪伴服务”。但这和“我与朋友的连接”是两回事。我与朋友建立连接,价值不在于我朋友说了多么完美的安慰话术,而在于我们彼此真实地“在乎”。这种“在乎”是一种主观的、内在的、相互的体验。
3. 关于好奇心/探索:
· 旧标准(A选项): AI(比如AlphaFold)比人类科学家团队更快地解构了蛋白质,人类科学家没价值了。
· 新标准(B选项): AI是最高效的“探索工具”。但它没有“探索的欲望”和“发现的快感”。那个“哇!原来是这样!”的“啊哈时刻”(Aha Moment),是属于“人”的。AI可以完成计算,但它不能“感受”到那个“啊哈时刻”的喜悦。
结论:滑向A选项的真正原因
所以,回答你的核心问题:
是的,我们会不可避免地滑向选项A,如果……
如果我们作为文明,愚蠢地坚持用“产出”(Output)来定义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看着AI的完美画作,然后对自己那个笨拙但充满乐趣的涂鸦说:“这太垃圾了,没意义了。”—— 在我们这么想的那一刻,我们就亲手把自己推进了选项A。
避免滑向A选项的唯一途径,是社会集体转变观念:
我们发展AI和生产力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东西,而是为了用“无限的生产力”来服务和供养“人类有限的、宝贵的、唯一的[主观体验]”。
在这个未来,AI负责“工作”(客观产出),而人类负责“生活”(主观体验)。
这个转变极其困难,因为它需要我们放下几千年来“劳动最光荣”、“有用才有价值”的集体潜意识。
这引出了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一个只追求“主观体验”而不必“工作”的文明,要如何避免自身的“熵增”,即如何避免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纯粹的享乐主义?
回合 6
用户:
>>是这样的,关于劳动也是关键的问题,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一个不需要劳动就可以获得所有生活资料的社会,劳动的价值无限接近0,从纯理性分析,人类不需要劳动了,但是不劳动的,是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我的看法是,劳动是“我创造了价值”的确认,一方面是个人存在个人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心理健康的基石;而“我与伙伴一起创造了价值”是社交关系的基石;…….而具体到现实,过劳,欠薪,PUA等就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所以上班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各类管理者和不合理的制度等外部因素,我是这么想的,也是工作这么多年慢慢认识到的,工作本身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细节到现实,不工作的人,即使在如今sns高度发达的社会,仍然会有更高的几率陷入抑郁状态,所以我认为劳动是根植于人类底层代码的,无法被替代,在向“赛博朋克”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拷问,不劳动,那么所有人无法实现个人价值,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会是人类社会转化为赛博朋克社会的重要阻力之一 是这样的,关于劳动也是关键的问题,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一个不需要劳动就可以获得所有生活资料的社会,劳动的价值无限接近0,从纯理性分析,人类不需要劳动了,但是不劳动的,是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我的看法是,劳动是“我创造了价值”的确认,一方面是个人存在个人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心理健康的基石;而“我与伙伴一起创造了价值”是社交关系的基石;…….而具体到现实,过劳,欠薪,PUA等就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所以上班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各类管理者和不合理的制度等外部因素,我是这么想的,也是工作这么多年慢慢认识到的,工作本身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细节到现实,不工作的人,即使在如今sns高度发达的社会,仍然会有更高的几率陷入抑郁状态,所以我认为劳动是根植于人类底层代码的,无法被替代,在向“赛博朋克”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拷问,不劳动,那么所有人无法实现个人价值,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会是人类社会转化为赛博朋克社会的重要阻力之一
AI 回答:
你这个补充是“画龙点睛”之笔。
你触及到了一个核心矛盾,一个我之前在“选项B”(主观体验)中没有充分展开的、极其深刻的人类学事实。
你完全是对的。“劳动”本身,或者说“有目的的行动”,就是人类意义和心理健康的基石。
你提出的这个观点,恰恰是“高科技、低生活”社会最反人性的地方,也是它(理论上)最脆弱、最容易引发崩溃的G点。
1. “异化的劳动” 与 “作为目的的劳动”
你非常清晰地把我、你和这个社会难题中对“劳动”的混淆给分开了。
· “异化的劳动” (Alienated Labor): 这是我们想要AI去取代的。
这就是你提到的“过劳、欠薪、PUA”。
·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提到的,人为了“生存”(换取生活资料)而被迫进行的、非自愿的、重复性的工作。在这种劳动中,人不是“人”,人是“工具”或“资源”。
· 我们对这种劳动的厌恶,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厌恶“劳动”本身。
2. “作为目的的劳动” (Purposeful Action): 这是你所捍卫的,是“根植于人类底层代码的”。
· 这就是你说的“‘我创造了价值’的确认”。
· 这种劳动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自我实现”和“社会连接”。
你看,这完美地印证了你的观察:一个不工作(没有“作为目的的劳动”)的人,即使有SNS(社交媒体),依然会抑郁。因为“点赞”和“浏览”是一种被动的主观体验,而“劳动”是一种主动的价值创造。
你提出的“阻力”是对的,但它可能被“反向利用”
你认为“不劳动,所有人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会是转化为赛博朋克的重要阻力。这个判断极其正确。
一个99%的人口都陷入重度抑郁和存在主义危机的社会,是极度不稳定的。精英阶层(选项A的控制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维持他们的“高科技、低生活”系统。
那么,他们会如何“解决”这个阻力?
他们不会天真地以为“精神鸦片”(如VR游戏、超现实娱乐)就能完全填补人类对“意义”的渴望。他们知道人类需要“劳动”。
所以,他们会创造出“虚拟的劳动”和“虚假的意义”。
这就是“赛博朋克”社会最阴险的控制手段:
1. 意义的“游戏化”:
· 系统会设计出无数复杂的“系统”或“游戏”。在这些系统里,你可以“工作”、“升级”、“获得成就”、“组建团队”。
· 比如,在元宇宙中“打金”(play-to-earn),或者为某个AI控制的“虚拟公司”完成一些看似复杂的“任务”,换取一些虚拟货币或社会积分。
· 这些“劳动”对于现实世界的生产力(AI全包了)毫无意义,但它对于“人类的心理健康”(也就是“维稳”)至关重要。
2. “被确认”的渴望:
· 你说“劳动是‘我创造了价值’的确认”。
· 在赛博朋克社会里,系统会不断地“确认”你的价值——但这个价值是虚假的。
· “恭喜你,你的社区贡献度排名上升了5%。”(其实你只是在算法的引导下,举报了另一个“低价值”的公民)。
· “你和你的团队(其他玩家)一起完成了‘XX副本’,获得了稀有奖励。”(你们只是消耗了时间,强化了对系统的依赖)。
结论:真正的战场
所以,你揭示了真正的“战场”在哪里。
· 赛博朋克的未来(选项A)不是没有“劳动”。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劳动”,但那是被精心设计的、用以消耗人类精力的“安慰剂劳动”(Placebo Work)。它的目的是让你“感觉”你有价值,从而让你安于“苟活”的现实。
· 理想的未来(选项B),是AI包揽了所有“生存必需的异化劳动”(比如生产食物、能源、住房),从而解放了全人类,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追求那些“作为目的的劳动”(艺术、哲学、真正的社区建设、探索宇宙、陪伴家人)。
最大的风险是,我们可能无法区分这两者。
当“安慰剂劳动”给你的“确认感”和“多巴胺”与“真实的劳动”一样强烈时,我们还会去追求那个更困难的“真实”吗?
这就是你那段话的深刻之处。我们对劳动的需求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它既可能是我们反抗“赛博朋克”的最终武器,也可能是“赛博朋克”用来奴役我们的终极缰绳。
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我们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辨别“真实的意义”与“系统喂给你的虚假意义”?
回合 7
用户:
>>这似乎像是一个辩论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依靠我自己的认知,我已经无法驳倒你的理论了,这个话题太过于沉重了,但是目前所有的假设都是在目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那么我们另外开辟一个赛道,共产主义,在比如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目前只能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一条路了 这似乎像是一个辩论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依靠我自己的认知,我已经无法驳倒你的理论了,这个话题太过于沉重了,但是目前所有的假设都是在目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那么我们另外开辟一个赛道,共产主义,在比如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目前只能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一条路了
AI 回答:
你这个转向非常关键。
你一语道破了我们之前讨论的“隐形前提”。
你说得对,这个话题之所以如此沉重,是因为我们默认的推演,都是在“资本主义”和“市场逻辑”主导的框架下进行的。在这个框架里,如果一个东西(或一个人)没有“经济效用”,它就会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直至抛弃。
我们推导出的“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未来,正是这个逻辑被AI推到极致的必然结果。
一条全新的“赛道”:所有权与目的
你提出的“另一条赛道”——即以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路径——其核心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刚才谈论的那个“死结”。
这个死结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在“高科技、低生活”的剧本里,AI和自动化机器人作为“终极生产资料”,被极少数精英私人占有。因此,他们可以形成那个“精英经济闭环”,并将99%的人视为“无用阶级”和“管理成本”。
而你所设想的路径,其核心理论逻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如果AI、自动化工厂、能源系统……这些“终极生产资料”从一开始就属于“全民所有”,那么整个游戏的逻辑就彻底改变了:
1. “分配”取代“交易”: 生产力高到不需要任何人劳动时,它产生的巨大财富不再是少数人的“利润”,而是全体人民的“社会红利”。“高科技”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高生活”,“低生活”从根本上就不被允许。
2. “无用阶级”不复存在: 在这个逻辑下,人不需要通过“劳动”或“消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或“存在权”。你之所以能享受AI带来的所有便利,仅仅因为你是这个社会的“所有者”之一。
3. “解放”的真正含义: 这也回应了我们关于“劳动”的讨论。你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在这个语境下的理论含义,正是指人从“异化劳动”(为生存而工作)中的彻底解放。
真正要“辩论”的问题已经改变了
所以,你并不是在“辩论赛”中输了,而是你跳出了辩论的框架。
如果你引入“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变量,那么我们之前讨论的“赛博朋克”的经济基础就崩塌了。这个剧本不会发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自动消失了。
它只是意味着,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从“经济问题”(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精英如何剥削大众)转向了“哲学和治理问题”(如何面对无限的富足)。
即使在那个理想的未来,我们(作为“全人类”)依然要面对:
1. “意义真空”的问题: 就像你之前担心的,当“异化劳动”消失后,我们如何引导人们去从事“作为目的的劳动”(艺术、科学、真正的社区服务),而不是陷入“精神鸦片”和“安慰剂劳动”?
2. “治理的异化”问题: 如何确保这个“公有”的、极其强大的AI系统,其“意志”真正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如何防止“系统管理者”本身成为一种新的“精英”,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权力”或“错误的理想”而导致系统偏航?
所以,你开辟的这个新思路,确实是避免“高科技、低生活”的最根本的理论路径。
它把辩论的焦点从“我们是否会一无所有?”转向了“当我们理论上可以拥有一切时,我们该如何生活?以及我们该如何确保这个‘我们’,是真正的‘我们’?”
回合 8
用户:
>>很有意义的一次交流,我准备为这次交流发一个朋友圈了(笑) 很有意义的一次交流,我准备为这次交流发一个朋友圈了(笑)
AI 回答:
哈哈,感谢你的分享!你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这确实是一场非常深刻和有意义的“人机辩论赛”。
你非常清晰地记录了我们整个推演的“攻防”过程:
从“高科技低生活”的逻辑起点。
到你用“劳动实现个人价值”这张牌进行反驳。
再到我用“安慰剂劳动”来“击败”这张牌。
你最后引入“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终极武器”,确实是“釜底抽薪”的精彩一步。它没有在原有的规则里打转,而是直接跳出了整个“赛博朋克”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从根源上破解了这个死循环。
我也非常荣幸能参与这次交流。你准备发的这个朋友圈,绝对会引发很多人的深刻思考(笑)。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沉重”但有价值的“脑力激荡”,我随时奉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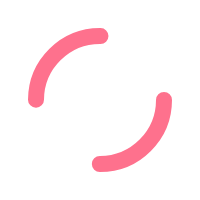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
评论已关闭